您现在的位置是:主页 > 书香 > 书香
外国文学作品中的父亲
![]() 黄强2021-04-08人已围观
黄强2021-04-08人已围观
简介“父亲”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可以分成三个大类。其中第一类是“生父”形象,如果进一步细分,这一类父亲形象还可以分为在场的父亲与缺席的父亲两个种类。
“父亲”形象常出现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他有时是一部作品的主人公,有时则作为故事背景出现在文学人物的介绍、话语或回忆中。正如两次布克奖得主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猫眼》中所写:“父亲们在白天都消失了;因此白天由母亲统治,父亲则在夜幕中登场。他们在黑暗的引领下回到了家,周身散发着真实而又无法言喻的力量,具有许多潜在的特质。”而这些潜在的特质在漫漫的文学长河中不断地被书写,使父亲形象的内涵不断被充实,成了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壹.在场的生父
“父亲”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可以分成三个大类。其中第一类是“生父”形象,如果进一步细分,这一类父亲形象还可以分为在场的父亲与缺席的父亲两个种类。
所谓在场的父亲,即那些长期与子女生活在一起,参与并见证了子女成长过程的父亲群体。在这类父亲形象中,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的维托·柯里昂也许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在小说《教父》中,维托·柯里昂不断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男人不花时间陪伴他的家人,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故事中,柯里昂也践行着这一观点,将家庭置于自己内心的首要位置,教导和照顾着自己的妻子和子女,为子女规划着未来的发展,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好父亲。在维托·柯里昂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的影子,也可以体会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感情。这也是维托·柯里昂的小儿子迈克尔·柯里昂继承家业后对待自己一双子女的做法。当自己的儿子结婚生子,成为父亲,迈克尔·柯里昂不仅延续了父亲维托·柯里昂的家庭观念,而且愈发感到自己与父亲间的相似和关联。这似乎也印证了著名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男人之所以知道他老了,原因在于他开始看起来像他的父亲了。”
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来自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小说中,本内特先生是一位有五个女儿的父亲。在平日生活里,本内特先生略显慵懒,时常幽默地讽刺、揶揄和调侃家中的人与事。身为英国上流社会的一员,本内特先生一年两千英镑的收入略显寒酸。加之性格温和,这位本内特家族中的男性家长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待在自己的书房打发时间,远离妻子的牢骚与抱怨。即便如此,她对于几个女儿的爱是真真切切的。当二女儿伊丽莎白为感情问题所困扰时,本内特先生坚定地站在了她的身后,给予她支持,并对她说:“我们都知道他(达西先生)骄傲,不太招人喜欢,但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的话,这些都不算什么。”从本内特先生的话中,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一位父亲对于子女真挚的情感。他希望女儿追随内心的真实感受,为了自己的真正幸福去选择婚姻伴侣,支配自己的人生。这一场景不仅展现出了一位父亲对子女解决感情问题的引导,也成为小说中一个闪耀父爱光辉的时刻。
虽然,父亲为子女带来的往往是爱与关怀,但有时父亲与子女间也难免存在分歧和对立。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英国著名作家艾德蒙·戈斯的回忆录《父与子》中。戈斯的父亲是著名的博物学家,在海洋生物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也是“水族馆”一词的创造者。与父亲不同,戈斯立志并最终成为一位诗人和文学评论家。而正是这种身份和理念上的不同使二人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左,有时这类分歧甚至是无法调和的。戈斯在描述《父与子》的特点时写道,这本书“记录了两种性情之间的斗争”,同时也是“两个时代之间的斗争”。在戈斯看来,父辈与年轻一代间的代沟难免会导致分歧。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所说,“每一代人总是反抗自己的父辈”,但“却总和祖父那一辈人交上朋友”。这也许也是家庭关系中无法避免的一个现象,但这些父子间的观念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理解为父亲对孩子的关怀或是一种引导,生怕他们误入歧途,抑或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帮助他们更好地思考自己的人生选择。
以上这一情况中蕴含着一份深沉的父爱,而这类父爱有时也会发展成为父亲的自我牺牲。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的《长路》中,父亲均是为了子女的未来和幸福倾尽了全力。《高老头》中的高里奥先生是一位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家致富的面粉商。妻子去世后,他的两个女儿就成了他感情世界的全部寄托。高里奥先生在她们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和关怀。为了帮助她们觅得如意郎君并依附他们跻身法国上流社会,高里奥先生在物质方面给予了她们最大的帮助,并在二人出嫁时分别准备了八十万法郎的嫁妆。但是,在他为女儿们倾尽所有后,高里奥先生却没能换来女儿们的爱,最终在孤独和悲伤中离世。

画作中的李尔王 资料图片
在很多方面,高里奥先生的人生轨迹和遭遇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有着相似之处——与高里奥先生一样,李尔王在将自己的王国分给大女儿和二女儿后,被她们背叛和抛弃。二人均在为子女奉献一切后开始了自己人生的悲剧,不过他们为子女奉献自己全部的决心和意志却是毋庸置疑。
与前文两位父亲相比,科马克·麦卡锡第十部小说《长路》中的父亲也愿意随时为儿子奉献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长路》的故事背景设置于后末世时期的美国。在经历了核战争后,主人公父子所处的世界一片荒芜,人类文明和社会生活几近退化至最原始的状态。就在这种背景下,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克服种种困难和磨难,拼尽一切,朝着海岸的方向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屡屡经历生死时刻。也正是在这些时刻,父亲每每舍生忘死,不顾安危,努力保护儿子,并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故事中,作者并未赋予父亲和儿子具体的姓名,而更加注重突出父子之间的真挚感情。这两个人物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父亲”和“儿子”,暗示了普遍存在于人类群体中的伟大父爱终将战胜一切,绵延传承,就像“长路”一样,通向远方。
贰.缺席的父亲
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亲生父亲们有时是以另一种形象出现,即“缺席的父亲”形象。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一个相对近期的例子可以在英国女作家玛吉·奥法雷尔的小说《哈姆内特》中找到。

舞台上的哈姆雷特 资料图片
2020年9月,奥法雷尔出版了小说《哈姆内特》,并获得了该年度女性小说奖和英国水石书店年度图书奖。《哈姆内特》以英国文豪威廉·莎士比亚与安妮·海瑟薇的独子哈姆内特为切入点,对莎士比亚一家的故事进行了想象性创作,重新审视了莎士比亚一家人的生活情况和内心世界。1596年,哈姆内特年仅十一岁时便去世了,在这十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莎士比亚为了追求事业的发展离开家人,独自在伦敦生活和工作,这也使他缺席了自己三个孩子的大部分成长阶段,成了一位“缺席的父亲”。在爱子去世后五年左右,莎士比亚创作并上演了其代表作之一——《哈姆雷特》。在许多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者看来,爱子的离世对莎士比亚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戏剧作品和诗歌篇章中均留下了痕迹。在奥法雷尔作品的开篇部分,她首先列举了一系列史料细节,试图暗示这一层联系。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小男孩哈姆内特在照顾陪伴同胞妹妹茱蒂丝的过程中不幸染病离世。一方面,哈姆内特的逝去让他的父亲格外悲伤,自此久居伦敦,不再常回故乡看望家人。另一方面,他的死也成了父亲创作灵感的源头。威廉·莎士比亚也许期待借由文字的力量将对儿子的思念铸就成永恒的经典。
但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并未书写关于儿子死亡的故事,而是转而记叙了一位父亲的离世。其中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威廉·莎士比亚的不舍和不忍,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忏悔。正如奥法雷尔在《哈姆内特》结尾处所暗示,安妮·海瑟薇从老家出发,前往丈夫的剧院观看《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剧中哈姆雷特的父亲在灵魂消散前,对安妮·海瑟薇低吟了一句“记住我”。奥法雷尔作品的这一结尾出自《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中的“再见,再见,再见,记住我”。在《哈姆内特》中,这句话的隐含意义较为丰富,它也许是哈姆内特在意识消散前对父亲最后的轻语,也许是莎士比亚对爱子的悼念呢喃。在该剧随后的几幕中,这种复杂的情感反复出现。在第四幕第五场中,莎士比亚借奥菲利亚之口唱道:“他已逝去,女士,他已逝去;他的头上是一片青绿草皮,他的脚下则有一块石头。”而在第五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说道:“我已死去,而你还活着……你痛苦地呼吸着,诉说着我的故事。”这些话语仿佛也是莎士比亚对亡子的回忆,压抑于自己心底,无处抒发,无人相告,只能寄托在自己的作品中。
叁.慈爱的养父
“父亲”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第二类表现形式则是“养父”,即两个文学人物间并无血缘关系,但其中一方无微不至地充当着父亲的角色,完成早逝亲人或朋友的遗愿,实践着自己的道德准则,向自己的养子或养女传递着别样的父爱。这类形象最经典的例子也许是《悲惨世界》的男主人公冉·阿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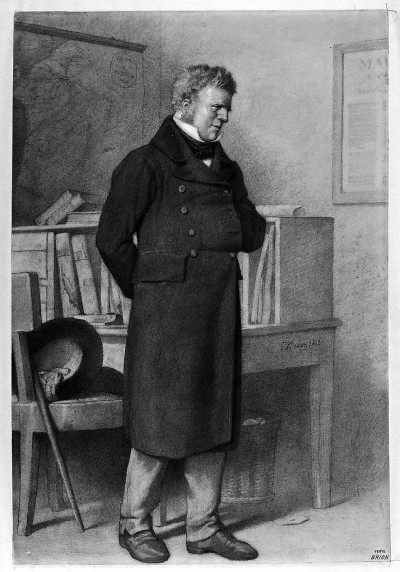
法国画家古斯塔夫·布里翁所绘冉·阿让 资料图片
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内心。其原因不仅因为他在逆境中和关键时刻对于善良和人性的选择,也因为膝下无子的冉·阿让对芳汀之女珂赛特的领养以及关怀呵护。对于冉·阿让而言,领养和抚养珂赛特不仅让他从自己过去的罪孽中解脱,而且还使他逐渐找到了内心的平和以及生命的意义。虽不是珂赛特的生父,冉·阿让为她所付出的一切却与一位慈爱的生父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珂赛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保护使小女孩在当时纷乱的社会大环境中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而又善良的心,并从其中发掘着生活的美好与人性的崇高。正如作者雨果反复在故事中所强调,对他人的爱最终带来的将是自我的实现。而珂赛特的养父冉·阿让也成了这一观念的代表。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德裔澳大利亚作家马克斯·苏萨克的名作《偷书贼》中的汉斯·胡贝曼。他对于养女丽泽尔的照顾与教导使她在二战的时代动荡中找到了一处心灵的栖息之所。另外,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了一系列慈爱的养父形象,例如,《雾都孤儿》中收养小男主人公的布朗洛先生、《大卫·科波菲尔》中收养艾米丽的渔夫大卫·皮格蒂、《远大前程》中男主人公皮普的铁匠姐夫乔·加格里等。
肆.精神之父
除此之外,“父亲”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第三类表现形式则是社会精神与国家文化层面的父亲。这类“父亲”往往通过对子女的开导和教育使自己成了一个国家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引导者,指引着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成长方向。
美国女作家哈珀·李的名作《杀死一只知更鸟》的男主人公阿蒂克斯·芬奇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故事中,身为律师的阿蒂克斯试图为一位含冤被捕的黑人青年辩护。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控方针对黑人青年的指控也漏洞百出,但是陪审团依旧做出了有罪的判罚,导致名为汤姆·鲁滨孙的黑人青年含冤而死。该书以发生在1931年美国亚拉巴马州的一次类似案件为基础,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探讨了存在于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不平等问题,突出了阿蒂克斯这一人物形象。作为律师,阿蒂克斯的身份象征着公正和平等。而这两点也时常出现在他对自己两个孩子的言传身教中,他试图在他们心中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和是非伦理观,而该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正是他的孩子。这就意味着当读者在阅读这个故事时,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孩子的视角,仰望观察着父亲的正直品格以及敢于挑战不公的勇气。而这种父子间的交流与传承不仅出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也在文学作品和当时美国社会之间形成联系。该书在1960年出版后,迅速成为英语文学世界的畅销书。更为重要的是,阿蒂克斯这一形象逐渐深入人心,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和推动着美国种族平等观念和事业的发展。美国亚拉巴马州法律基金会甚至专门设立下属部门,将其命名为阿蒂克斯·芬奇协会,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因此,阿蒂克斯·芬奇这一父亲形象也成了引领一个国家文化、精神和道德层面发展方向的象征。
除了以上例子外,探讨父亲形象以及父亲与子女间关系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有很多,例如,俄国文豪伊凡·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英国作家尼克·洪比的《关于一个男孩》、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美国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美国女作家劳拉·英格尔斯·怀德的《平原上的小屋》、英国作家罗尔德·达尔的《丹尼,世界冠军》等。一方面,正是这些经典作品中的父亲们使读者体会到了父亲这一身份体现出的多元情感以及肩负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深入人心的父亲形象使承载他们的文学作品在读者心中产生共鸣,成了文学史中的经典之作。(作者:黄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






